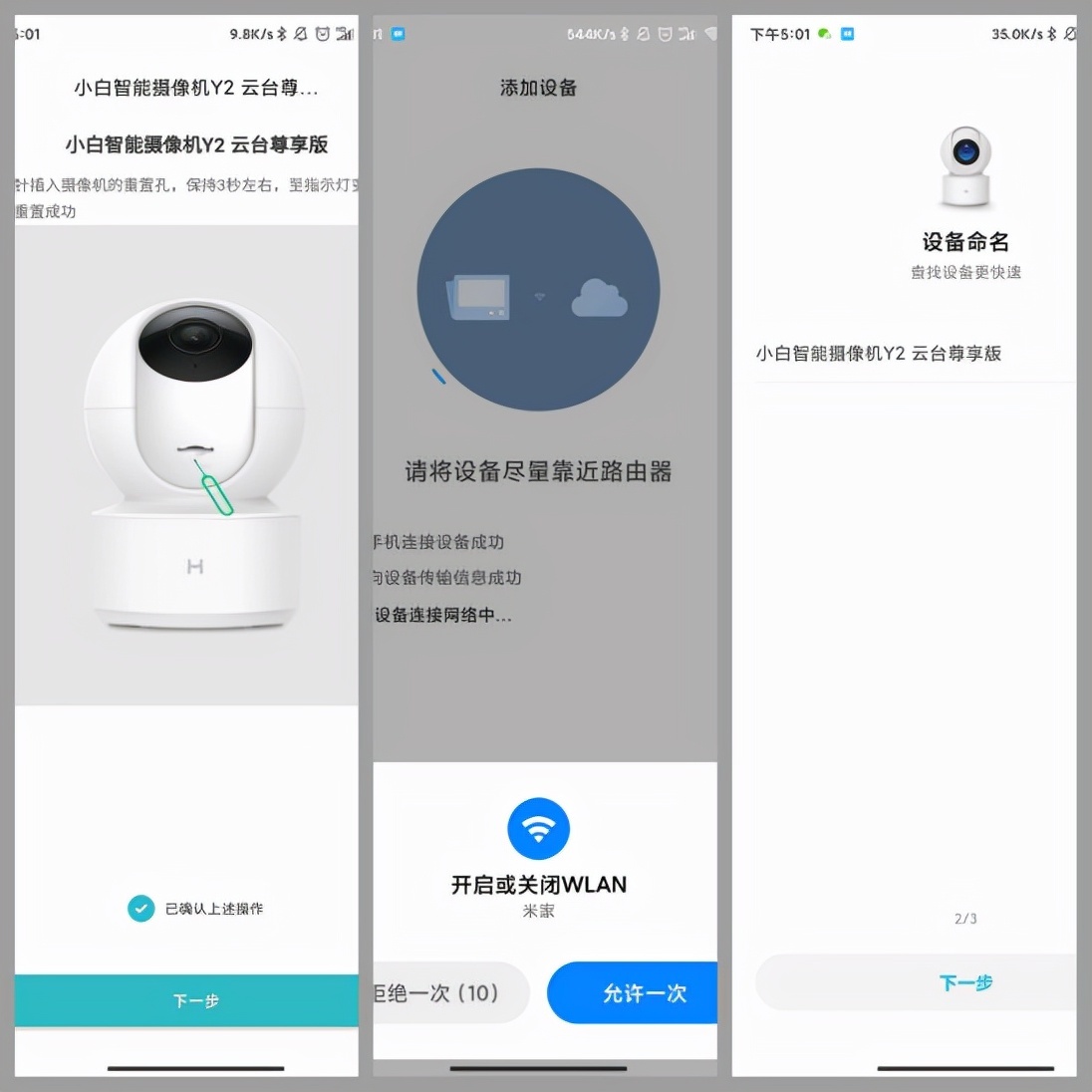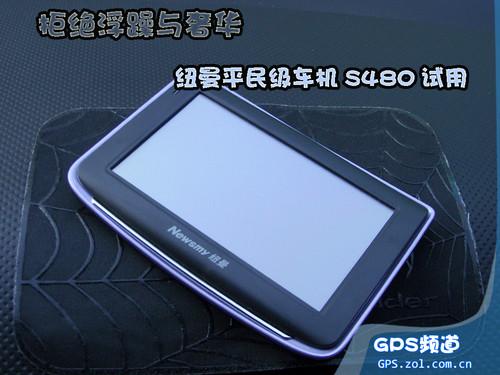养老院内,90岁的王奶奶像往常一样,熟练地站上平衡训练与测试系统,点开屏幕上的切水果游戏,“你看这样摆动一下胯部,一下子能‘切’好多水果。”银白的发丝随着她的动作轻轻摆动,“以前单脚站着打晃,‘玩’了这款游戏之后,现在我单脚能站稳了。”
养老科技产品能给老人们带来什么?答案不只“更健康”,还一定有“更快乐”。随着上海养老科技产业园的建设,一批来自于实验室的创新产品进入社区、养老院试用,老人们爱玩的热情、使用的频次,正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检验,成为产品持续迭代优化的有力依据。
跌倒是老年人最常见的伤害,一次小小的跌倒,就可能造成严重的损伤。在王奶奶看似轻松的游戏时刻背后,却是一次跌倒风险的降低。据君莲养老院院长诸培红介绍,这套防跌倒“筛查—训练”系统已为100余位长者服务,对于下肢力量的改善效果显著。
这类巧妙将康复训练融入趣味游戏的装置,深受老人欢迎——特别是相对年轻、活动能力较好的长者。其中,防跌倒平衡训练系统和三维动作捕捉分析系统凭借超高的使用频次,稳稳荣登养老院康复设备的“爆款”前列。
轻量化的装备,也正在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带来重获行动能力的希望。重量约2kg的外骨骼机器人,通过AI算法与传感器融合,让很多需要搀扶才能挪步的老人,重新感受到行走的喜悦。某社区医院康复训练室,63岁的李阿姨正佩戴着康复型外骨骼机器人缓慢行走,经过5周训练,她因中风导致的左右腿不协调的步态已接近正常。
“院长,我可以申请使用纳米助浴吗?”“可以,但是需要排队。”记者探访发现,在君莲养老院引进的39款产品中,纳米助浴项目格外受长辈的青睐,这款主打“一瓶水、一个人、一刻钟,洗净全身”的助浴产品,不仅在养老院是热门体验项目,走进社区后更成了“网红”。“像是做了一次温热的深层SPA,洗完后皮肤滑滑的,头发也很柔顺。”
PG电子据介绍,养老院每周开放两个半天的体验时段,每次最多可服务12位老人。目前已有近200位长者参与体验,预约持续火爆,处于“供不应求”状态。“传统助浴需多人协作,尤其是针对那些在床上行动不便的老人,而纳米洗浴仅需1到2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操作,节省了人力成本,也减少了老人滑倒的风险。”诸培红解释道。
“搭配艾灸机器人的,还有我们的智能AI舌诊仪、AI按摩机器人。”莘乐里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王旭艳介绍,舌诊仪能提供辅助诊断结果和健康调理方案,大大减少了对专业人力的依赖,普通的养老护理员或工作人员只需经过一周培训,就能熟练操作这些设备,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安全、舒适的专业理疗服务。
当这些“叫好”的科技产品试图从养老院、社区试点走向更广阔的市场,从“试用”迈向大规模“使用”时,一道“成本关”横亘在面前。
以纳米助浴为例,其研发企业中进宏康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庆飞告诉记者,传统浴缸助浴模式下,一次洗浴的费用通常在450—500元之间,而纳米助浴技术的出现,将单次服务价格降低至299元。尽管降幅明显,但对于许多老人及其家属而言,这仍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
“洗个澡299元,还是太贵!”面对老人家属的吐槽,丁庆飞无奈地算了一笔账:2位助浴师的人工费由当天单量决定,每单工费平均在100—150元,设备损耗与耗材大概在50元,还要算上运营人员与设备闲置成本,企业虽然想最大程度让利于民,但不得不考虑长久运营成本。
“并不是没有办法。”丁庆飞提出两条可行路径:一是形成规模,如果每月有2000名失能失智老人或重度残障人士接受服务,按每人每月洗2次的频次计算,人工与机器成本就能被大幅摊薄,单次费用自然下降;二是多元支付,如果能通过政府消费券、长护险或医保按比例报销,个人自付部分也能进一步降低。
费用高似乎是很多养老科技产品的通病,“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平衡高昂的设备成本与老人家庭的支付意愿。”大华福利院院长杨蔚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,养老院曾引进几台单价万元以上的高级护理床,能够实施监护老人状态并进行压疮护理,使用到这张床的老人家庭仅需要支付每天10元的个性化服务费,每个月就是300元。“但事实证明,他们宁愿拿这个钱换一个舒适点的房间。”
诸培红对此也有同感,“再智能化的设备也离不开人工照护,一些高端智能化产品定价低则两三万,高则十几万元,即便功能先进,或许只适合有经济能力的家庭自主购买,难以在普惠性的养老机构或普通家庭普及。”多重因素叠加下,智能设备进入养老院、社区的“成本关”,依然是横亘在众多机构面前的现实挑战。
如何让更多养老科技产品跨越“付费意愿”的鸿沟,真正惠及更广泛群体?关键在于解决“产品如何做”和“谁来买单、如何推广”的难题,养老一线从业者和专家指出,产品优化与市场培育是破局的关键。
“技术再好,脱离老人真实场景和感受,也难以长久。”杨蔚把安全、稳定、普适设为引进养老院产品的三道硬门槛,“一款产品进入市场应该是起点,产品研发必须持续优化设计,紧密围绕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迭代升级。”换句话说,做养老科技产品的人,既要懂技术和市场,更要懂老人。
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曹凯同样提到,“养老科技研发必须深度适配老人的身体能力、心理期待和社会情境”。他发现,老年人对新科技的接受度受多重因素制约,包括产品成熟度不足、心理适应周期较长以及市场推广力度不足等。“一些国外技术如果没有做好本土化调研,很容易偏离老人的真实需求,而面向失智失能群体的产品,常常因缺乏有效渠道获取真实反馈而阻碍优化。”
有了适配需求的产品,如何打开市场?在丁庆飞看来,首要问题是明确市场化运营主体,如果养老院或社区直接运营,势必面临成本与可持续性的双重压力,可以考虑将服务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,由后者提供人力与设备,而养老机构则负责制定指导价、加强监管并提升推广效率。“市场会一步步测试出产品合适的价格,相信‘老人愿意消费、子女愿意买单、企业又不会亏本’的平衡点很快会出现。”
相较于“谁来运营”,拥有8年一线经验、服务过上千名老人的吕雪莹则更关注“谁来买单”,她观察到,现在的老人们普遍对价格比较敏感。同时,很多企业依赖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,普遍反映直接向C端(最终消费者)销售产品和服务困难重重。
“如果一款产品的通用性足够强,老年人可以只是一部分受众群。”杨蔚进一步提出建议,“与其研发仅服务老人的小众产品,不如打造适应更广泛人群(包括老年人)的解决方案,这样既能摊薄成本,也更容易规模化推广。”